紀念“隴上鐵漢”安維峻誕辰157周年系列文章之八
甘于清貧 一身正氣
牟增保
被時人譽為“隴上鐵漢”的清代福建道監察御史安維峻,以不畏權勢、直言上諫而名震中外,但他一生甘守清貧的貧困生活卻鮮為人知。
安維峻出生于一個貧窮的知識分子家庭。自幼聰明好學,五歲時就能認識對聯中的若干字。但由于家貧和戰亂的影響,流離轉徙,時常以耕廢讀,十五歲和父親避亂寓居縣城楊家巷,在屋檐下讀書學習,得到鄉賢巨譚的賞識收為學生,開始專一讀書,在歷次縣、州考試中都名列第一,在親友們資助下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同治十三年(1874),朝考一等第一名,分配到刑部任七品小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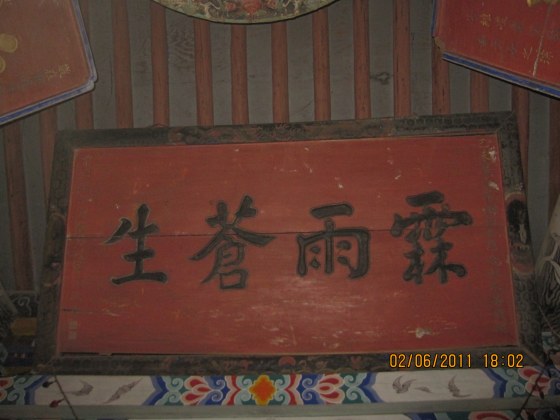
光緒元年(1875),他利用在家休假之機到吳可讀主講的蘭山書院求學。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閑暇時常去蘭山書院看望師生。對安維峻的人品和學識非常贊賞。因安維峻家貧,飲食常常難以為繼,左宗棠得知后,時常給予他以資助。他中舉人后,想繼續考取進士,因家中貧困沒有路費而欲放棄,在同窗好友王集邦的慷慨資助下才得以上京應試。不料安維峻上京后,連考兩科皆未中,左宗棠得知后,寫信安慰他,并在每年年底寄贈銀兩,解決他的日常所需。左宗棠對安維峻非常器重、關顧和激勵,并贈 “行無愧事,讀有用書”一聯,成為安維峻一生做人的信條。
他步入仕途之后,貧窮仍然如影隨形,這是一個清正廉潔的官員的必然處境。清代實行的是低俸制,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正從六品俸銀六十兩,米六十斛;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雍正年間,針對外官有養廉銀而京官沒有的狀況,京官實行雙俸制。這就是說安維峻的年薪是九十兩,米九十斛。但京官的俸祿往往是被打折扣分春秋兩次發放的,一般是六折發給。有不安于清貧的京官,就在地方官身上打主意,抓住他們的出格行為進行勒索,每年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日子過得倒也滋潤。但安維峻堅持操守,從不在歪門邪道上做文章,拿著被打了折扣的俸祿,過著居無定所、寄人籬下的漂泊生活,或留宿家鄉會館,或借居張育生、謝星海等朋友家,或客居所教學生家,每日精打細算,省吃儉用,勉強維持自身的生活。
清貧的生活使他幾乎沒有積蓄,每當家里開支較大或急需用錢的時候,他只得求親告友,或借或貸,然后發揮自己飽讀詩書的長處,開館授徒,用教書所得的酬金來償還債務。他曾經先后主講陜西味經書院、固原州五原書院、張家口掄才書院、隴西南安書院,晚年還在老家神明川村南關帝廟開辦私塾。由于勞累過度,以致患上了嚴重的痔疾,多年都未治愈。1890年,他的母親病故,此時家中一貧如洗,無力舉辦一個象樣的喪事,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經人介紹到天水書院閱卷得到七十兩的酬金才完結此事。他在祭母文中寫到:“母親舍不孝等而逝,計已逾十月矣,此十月家中之艱難,人情之冷暖,有不堪為母親告者……自五月起閱天水書院課卷,明年亦有書院可就,此乃年世誼中慷慨好義者扶持之力。……此后惟有努力活人,度此窮日以無貽。”由此可見當時安維峻窘迫的生活處境。安維峻一生清貧,但他從不隨便接受別人的饋贈和恩惠,在他因言獲罪流放軍臺時,甘肅各州縣同情他的遭遇,捐集白銀200兩贈送他,安維峻堅辭不受,并回信說:“費出無名,于理不順,于心不安,即當璧奉”。

晚清王朝內憂外患,政治腐敗,官場黑暗險惡,為官之道在于因循逢迎,明哲保身。只要對上司奴顏婢膝,左右逢源,必能步步高升。安維峻生性耿直,從不結交權貴,為人行事剛正不阿,與當時的官場格格不入。也有人提醒他和當權者交往,以求外放作地方官,他回答說:“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門生是不求者,此局并非圖外放,冀他日有所建白耳。”時任軍機大臣的張之萬想讓他拜在自己門下,李鴻藻想通過聯姻來拉攏他,都被他嚴詞拒絕了。公事之余,只與吳柳堂、周同候、徐仲文、龔鳳騫、滕玉堂等心性相投的有識之士談詩論文。因此仕途不暢,進京十多年后仍然是一個七品小京官。
監察御史是一個不受官場歡迎的角色,時人稱考御史為“走黑道”。御史雖然有議論朝政、參奏所有大臣們的特權,但稍有不慎,就會引火上身,招來殺身之禍。因此,大多數言官們為了自保,裝聾作啞,唯恐受到打擊報復。可安維峻安維峻置自己的毀譽得失、禍福生死于不顧,為他人所不敢為,言他人所不敢言,在短短的十四個月內前后共上疏六十余道,在疏中劾鹽務、錢法、學政等朝政積弊,彈劾大小臣工一百余人,涉及親王、軍機大臣、督臣等朝廷重臣,最后一道《請誅李鴻章書》,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清王朝的最高當權者慈禧太后和權傾一時的李鴻章,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光緒皇帝的斡旋之下,慈禧太后才法外開恩,同意發配他到張家口軍臺效力贖罪。安維峻在軍臺效力期間,更是窮困潦倒,靠主講掄才書院維持生活,同時也為人作書寫字,獲得微薄收入。在給李叔堅的信中說:“弟諸事如恒,惟牽于筆墨應酬,有日不暇給之勢。”他的詩作真實地反映了他的處境和思鄉之情:
倦仆中宵喚不應,
病妻強起為篝燈。
燒香默向蒼穹訴,
欲報春暉苦未能。
秦山隴水是吾鄉,
魂夢依依戀梓桑。
旅舍凄涼妻子共,
不堪著雨怨咨長。
退隱柏崖后的安維峻,其生活并不比當地的老百姓強多少。他家里人多地少,加之匪患頻仍,十年九旱,生活常常食不裹腹,因此他想盡一切辦法,組織村民興修水利,擴大灌溉面積,種植水稻,筑堡御匪,在小小的神明川踐行著他的安民濟世理想。據村里老人回憶,民國時期,安維峻的一個軍界朋友路過秦安,來看望他,他拿出家里僅存的高梁面,做了一鍋馓飯招待朋友,陳舊的高梁面馓飯霉味很重,這朋友才知道安維峻生活的艱難,于是就給他留下一些軍糧,做為接濟。
窮且彌堅,不墜青云之志。安維峻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斗爭精神,心憂天下、為民請命、抵御外侮的政治抱負將光耀古今,與世長存。他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甘于清貧的高尚的人格精神更是后世為官者的楷模和典范。
(作者系秦安縣地方志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