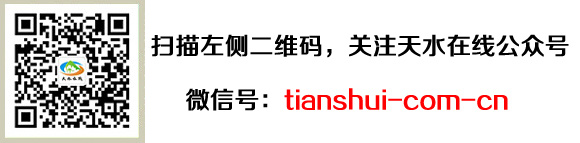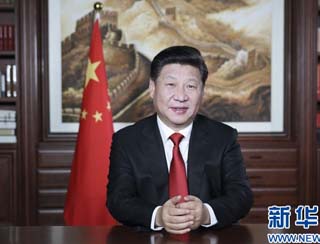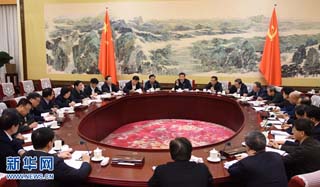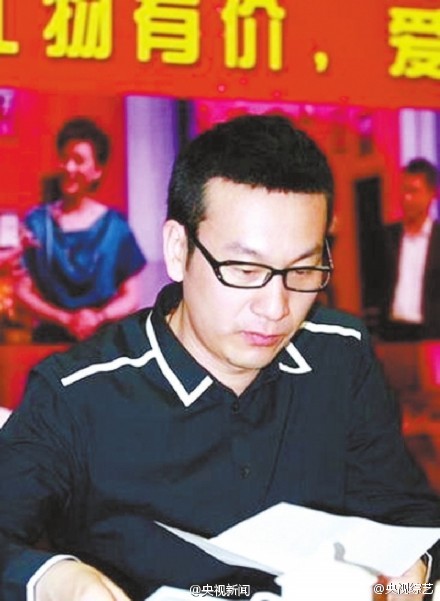離開兩年后,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李書磊重回北京。
這一次,他接下的是北京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的擔子。
據北京日報社旗下微信公號“長安街知事”1月3日深夜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準:李書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員、常委和市紀委書記,葉青純同志不再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委員和市紀委書記職務。
1964年出生的李書磊上一次離開北京前的職位是中央黨校副校長。他曾在這個副部級的職位上待了6年。
在這6年里,李書磊幾乎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他的低調,是任何場合的低調,絕非刻意掩飾”。
他的部下給出了6個字評價:嚴謹、低調、務實。
一
14歲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書磊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碩士、博士學位。
相比大多數同齡人,他要早上4年進大學,“神童”之名由此而來。
李書磊有一次對“神童”之名進行了解密:“我小學時連跳兩級。跳級是因為在班里學的東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過我了,聽課沒意思, 就逃學。逃學被老師逮著,我就裝病,裝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師告狀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讓我跳級,跳了級,課都是新的,都不會了,就不敢逃學了。”
讀小學時,李書磊并不是一個討老師喜歡的學生。
這點李書磊后來自己也承認:“老師不喜歡我,還老整我。我被同學評上‘五好’學生,老師卻把我‘拿’下了,我覺得很受傷害,天昏地暗。”
李書磊曾自稱“小孩兒里的文人”。
他上小學時的那個大隊叫破車莊,一個大隊有好幾個自然村,所以同學們來自不同的村子,兩撥小孩兒見面就大聲咳嗽,誰咳嗽得厲害誰就是爺爺,因為老爺爺們都咳嗽。往往見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戰。
李書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稱“文人”。
“文人”李書磊兒時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劍影”中虛度,李書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書。
“我把家里的書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記》《紅樓夢》,能找到的我都看。當時我最喜歡《西游記》了,看了就學孫悟空,撅斷我們家后院的小樹,把皮剝了,當金箍棒。”彼時,過日子受窮是大人的事,小孩子們總能自尋歡樂。
二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們視為幸運兒。
“文革”狂飆突起時,他們還小,受到的沖擊不大,也不用像他們的哥哥姐姐們一樣,早早地就上山下鄉了。
等到他們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時候,1977年,高考又恢復了,成績好的農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學,畢業后進入各個領域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1964年出生的李書磊都趕上了。
1978年,14歲的李書磊參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黃河灘上放羊,他姐姐拿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書的那一剎那,把羊鞭狂甩進黃河,“當時就想,這下子終于不用放羊了。”
為什么選擇北大?李書磊后來解釋過。
“在考大學之前,我在人民日報上看見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農兵學員高紅十和她的同學在討論長詩《理想之歌》的寫作。高紅十與《理想之歌》,我當然仰慕得很,但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詩,也不是詩人,而是他們圍著的那張桌子:桌子有光可鑒人的桌面,他們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級了。這桌子極大地打動了我,使我對北京大學產生了強烈的向往之心。”
李書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過,他的碩士和博士都選擇了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三
李書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同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時,李已經是中文系碩士一年級學生了。
換句話說,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師弟了。
孔慶東在一篇《北大博士李書磊的怪異風采》的文章中寫道:“李書磊在當今的青年學者圈里,屬于少年得志、官高爵顯的一位,我等文學青年皆以師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覺上,李書磊卻怎么看也并不像個師兄,連師弟也不像,說得冒犯一些,倒有點像師外甥——即某位師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慶東還記得,剛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溫儒敏老師說:“你們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帶一位研究生來給你們介紹學習經驗。”
到了晚上,溫老師領著一個白白胖胖的大孩子來了,說:“這就是你們的李書磊大哥哥。”
大家頓時好奇心起,心想別是溫老師上中學的兒子吧。一交談,“才知原來李書磊跟我同歲,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學——他是少年大學生”。
李書磊和那些“老三屆”同班,班里有的同學比他年紀大一倍,還有的女同學是帶著孩子來上北大的,孩子的戶口就落在他們班上……
師弟孔慶東回憶,“年輕的李書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個,但他似乎渾然不覺。他甚至不覺得自己年輕,他真的以一位兄長的態度給我們介紹北大的掌故,介紹他的研究課題。”
當時李正在研究20世紀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問題,他講得興致勃勃,眼鏡后面的小細眼睛笑瞇瞇地看著簇擁在他身旁的幾個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遠處的男生才是認真思考他的課題的,坐在近處的女生則大都是心懷叵測之徒。”孔慶東有點戲謔地寫道。
四
北大十年,同學們也教會了李書磊很多東西。
他們大都是高中畢業后闖蕩過一陣子的人,工農商學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們帶給李書磊的簡直是一部中國社會史。
李書磊后來談起這段歲月,“同學們的經歷與見識使我很快擺脫了中學時代通過報紙、課本認識世界的偏狹,加上當時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運動,我的思想與心智在不斷的驚愕中進步。”
畢業后的李書磊走了一條堅定的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1984年碩士畢業后,李書磊被分配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任教,兩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個博士學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黨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擔任中央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學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培訓部主任,中共中央黨校校務委員、培訓部主任,校務委員、教務部主任。
其間,他還曾先后赴河北青龍掛職縣委副書記,赴陜西西安掛職市委副書記。
2008年12月,年僅44歲的李書磊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官至副部級。其時,中央黨校校長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
五
盡管身居高位,在中央黨校同事心目中,李書磊還是習慣于用學者的語言與周圍人討論問題,而非官員的語言。
他通常的講話,只對一個問題進行學理分析,同時又能與黨的重大理論聯系起來。
李書磊常常說:“講話不能講滿,要留有余地。”
這個“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認為在你不能窮盡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時候,應該有學者的嚴謹,說滿口話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是李書磊在中央黨校具體分管的部門之一,在該部一位教師的印象里,李書磊幾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參加他分管領域的外事活動,他有著學者的嚴謹,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國友人來參訪黨校,送了李書磊一樣類似于當地土特產的東西,李書磊端在手里就問:“這個是吃的東西,還要交公嗎?”
這位教師還記得,每次黨建部青年教師的讀書會,李書磊幾乎都會來參加,不僅僅是聽,還會自己講。
“我們都很佩服他這點,雖然是文學專業出身,但他對政治學領域也有自己的學理思考。他往往從政治哲學的高度,能夠把我們的觀點包容進去,”這位教師說,“他的見地就是能把年輕教師吸引住。雖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稱號,但仍然會被他的超然稟賦折服。”
曾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提出中央黨校要成為一流學府。
習近平說,“一流學府”要體現在一流的教學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隊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礎設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務、一流的風氣和人文環境五個方面。
李書磊對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經常對教師們說:“外界評價中央黨校的老師講話敢講,我更希望外界說我們的老師很有學問。”
李書磊喜歡和年輕人聊些輕松話題,甚至不惜爆光一點自己當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讀書那會兒,如何當同學電燈泡的故事。李回憶說,那次當電燈泡最大的收獲就是吃了有生以來最香的一頓水餃。
他雖然允許年輕人犯些小錯誤,但該嚴格的時候還是很嚴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輕教師在說自己這一年發了多少多少文章,李書磊正好聽到,馬上指出:數量不是關鍵。
另外一次,一位年輕老師恰好發表了篇談石家莊的城市建設邏輯的文章,李書磊注意到了,專門找到那位年輕老師說,“你那個觀點不一定對,我們好好聊聊。”
李書磊對青年學者的關心還體現在生活上。他拿到經費首先會向青年學者傾斜,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最優秀的人到了我們黨校,如果我們不給他們機會,不關心、不培養他們,這是極不負責的行為,甚至是損陰德的事。”
話語間分量已經很重了。
七
李書磊的學問在學界一直頗受好評。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李書磊閉戶讀書,寫出了一系列重讀經典的好文章。
那個時候,“李書磊”三個字堪稱如雷貫耳,他的《為什么遠行》《雜覽主義》《重讀古典》《文學的文化含義》《我觀世音》等一系列書籍,不僅引起學界的注意,更在全國擁有相當可觀的粉絲讀者。
至今,豆瓣讀書上關于《重讀古典》一書的討論中,仍然可以看見有年輕讀者評價:“讀一下他的文章,我們就會知道李書磊的判斷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這兩年間,李書磊曾在北京西郊賃屋而居,不問世事,只在窗下苦讀古書。
“讀到感動之處,就特別想找人聊一聊,但沒有人,我就把心得寫成札記。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門,門外正紛紛揚揚地飄著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為什么,我竟淚流滿面。”李書磊說。
后來,李書磊把這些讀書札記整理發表,寫了一系列重讀古典文學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讀古典》。
李書磊從不否認自己著書是出于一種情感需要。“人過了25歲,滄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輕的時候,憑青春力量四處闖蕩的那個階段結束了,情感的浪漫主義也結束了。這時候,就特別需要一種情感的寄托、一種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對于國土的情感,對于中華民族的情感,包括對于中國經典和漢語的情感,才是我們真正的精神寄托。”
這種情懷在孔慶東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證:“每見書磊,他總是號召大家埋頭讀書,為國效勞,一副‘龍頭老大’的氣派。”
李書磊曾自稱最敬佩白居易。
他認為,白“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用佛家的無差別心洞見人生,他避免了人們常用的那種等級偏見”。從《琵琶行》到《長恨歌》,白居易不僅體察了下層的苦難,為歌妓的遭遇而濕了青衫,也還給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為一個帝王內心的痛苦與無助。
李書磊說:“這入骨三分的傾訴使我們對無限的人生肅然起敬,我們從這里讀出了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深深悲憫。”
 打印本頁
打印本頁